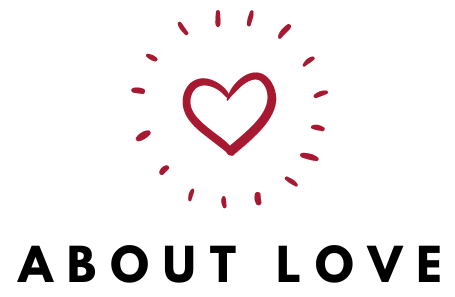公司十周年慶典,老闆海東青攜女伴姍姍來遲,給我們一票手下介紹。這是水靈玬。看見水靈玬那一瞬,我的眼眶微微發熱。海老大看向我, 吃了一驚。阿白,你怎麼哭了?
我嚇一跳,哭?誰哭了?抹一抹臉龐,一手的濕漉。尷尬的要死。趕緊告罪去了化妝間。對著鏡子訕笑,趙言白啊趙言白,又不是沒見過美女,激動成這個樣子?但那水靈玬真是美人,看一眼就知道。肌膚勝雪,五官立體,輪廓分明。一頭濃密的長髮,海藻般。名為水靈玬,偏偏又穿一件紅色吊帶裙子,細細的帶子在鎖骨處交叉向後。
很少看見有人能把紅色穿得那麼好看。我整理好走出去,酒會已經開始。賓客如雲。我神態自若地招呼客人。海老大抽空問我,我只答大概是昨晚沒睡好,剛剛燈光又太強烈之故。他點點頭,算是敷衍過去。那紅衣女郎將手輕輕搭在海老大的手臂上,沒有說話,笑臉盈盈。 很多女人似瓷娃娃,美則美矣,沒有靈魂。但這一位,一雙寶光流動的眼睛,未語先笑的紅唇。顛倒眾生。自信心稍弱的女人,看見她怕要去自殺。

我看看自己。永遠的黑白藍。眼鏡、髮髻、中性香水、素淨的臉。但我知道我和她原本是兩種極端。異性在她面前總是表現出最好一面, 然後和我互相拍擊後背稱兄道弟。我對自己很滿意。
我揉著兩邊的太陽穴開始叫。“饒了我吧。”電梯門打開,他拉著我走出去。冷笑數聲。“饒了你?哼,沒那麼容易。”他吩咐我的秘書。“Helen,給你們宿醉未醒的白大小姐泡點濃茶,她晚上還要去給臺灣客人陪酒。”Helen連聲應著,掩不住笑意。我咬牙切齒。“不要對我的秘書指手劃腳。”
他揚長而去。我在公司裡一向以冷靜理智著稱,遇事不慌不忙,處變不驚。只除了對酒精毫無抵抗力。像是白娘子,一碰雄黃便現出原形。所有情緒都白白寫在臉上。而海老大似乎以落井下石為樂趣。別看他平時西裝革履人模人樣一副成熟穩重的樣子,玩心一起,插科打諢極盡譏誚之能事。不知道的人還會贊他與下屬打成一片。 其實是以聯絡感情為名,行欺壓百姓之實。
可恥!

到午飯後才覺得精神爽朗起來。下班前略略整理儀容。當然海老大不可能真的叫我去給人陪酒。況且臺灣人受日本鬼子影響,大男子傾向嚴重,大概不會認同我也可以算是女人。 感謝上帝。飯局訂在全城最好的流轉壽司店。千鶴。幾乎所有臺灣人都愛這調調,真沒創意。公關部有人與我一起,席間總算是言談甚歡。點了日式燒酒,大家都知道我酒量甚差,每每技巧地替我擋著。我得以安然無恙。
我見時間差不多了,起身去了洗手間。不小心肩碰肩撞上一個人。我向後踉蹌幾步,一隻有力的大手緊緊拉住我。
“對不起。沒事吧?”頭頂一個低低的男聲。我穩住腳,直覺地護著皮包。眼鏡卻摔在地上。那人彎腰撿起來,檢查完好後才交還給我。我戴好眼鏡,抬頭見到那人,微微一愣。這人看起來至多二十七八歲,卻有一種滄桑的感覺。他穿一件黑色薄毛衣,咖啡色燈芯絨褲,外罩一件短風衣。也是黑色。濃密的黑髮, 略長,遮過頸部。卻並不顯淩亂累贅。還有一張瘦削而漂亮的臉、濃眉、薄唇、細長的眼睛。正是那雙眼睛,沉默、堅定,帶著溫柔的憂鬱。

“沒事吧?”這個有一雙禍水眼睛的男人重複道。我搖頭。“沒事。”
他點點頭。黑眸裡閃過一絲隱約的笑意。轉身走出店外。我深呼吸,平復內心的悸動。挑了挑眉,對自己說。就當是場豔遇吧。躺到床上時已經是淩晨時分,很疲倦。但那雙眼睛一直在眼前,揮之不去。我有絲驚異,那不過是個陌生人。
突然後知後覺地想起,他說的是韓語。天殺的!那個讓人心動的男人居然是我最最討厭的男人品種!要命,我要速速忘記他。
海老大大發慈悲,要請大家吃東西。有人提議去千鶴。我第一個舉手:“饒了我吧,我現在看見那個招牌就想吐。”這樣說好象蠻對不起那壽司師傅,但我不想再回到事發現場。過分神經質??小心駛得萬年船。結果我們去了另一家日本料理店。我原本不討厭吃日本菜,再無異議。跟在一群男生後頭走進店裡,不過停下來問了和服小姐幾句話。海老大在叫了。“阿白你還在磨蹭什麼?什麼不好學,學別人向美女搭訕。”

咖啡店裡飄蕩著柔和的音樂,我們兩個坐在靠窗的軟沙發裡。
“阿白,我那結婚禮物已經快發黴。”她開始老生長談。
我埋頭吃霜淇淋。“張老大怎麼忍受得了你?你一次比一次囉嗦。”
她瞪我。“你少來這一套。成天混在男人堆裡,也不知道順手抓一個。你以為你還經得起拖?”
“喂喂喂,別這樣說話。”我抗議。“人家會以為我做特種行業的。”
旁邊有人用餐巾掩著嘴咳嗽。我自眼角掃過去,是一名黑衣男子。echo大眼瞪著我,終於忍不住笑出來。echo是熱情如火的女子,愛恨分明。這些年來,她一直是我的陽光。我們準備走的時候,小姐微笑地說。“那位先生已經替二位買單了。”

我與echo大眼瞪小眼。呵,我們一起混這麼久,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難得我們一個男人婆,一個黃臉婦,居然還有這等榮幸。那黑衣男子似乎正與人談話。他朝我點頭示意,漂亮的臉上露出一個微笑。居然是他!那個“豔遇”。
害我一路上受echo嚴刑拷問。末了,她說,“我看這傢伙心懷不軌。你自己要當心。”
我鬼祟地笑。“幾分鐘前還有人叫我抓緊身邊的男人。你不是在嫉妒我吧?”
她橫我一眼。懶得理你!我送她到家。她拎著大包小包下車。走了兩步又回頭來,臉上是難得地認真。“阿白,答應我。小心那個洋鬼子。”

我不由自主點點頭。她滿意了。擺擺手讓我走。
慢,我有說過他是韓國人嗎?
若我問echo,她會說。“哼,還用得著說麼?看那一副低級的樣子就知道!”echo一向眼光獨到。說真的,我自己對這個人也有點不安。以一個陌生人而言,他實實在在帶給我意外的情感困擾。好在我不知道他是誰,而我也不認為我們還會有第三次的“偶遇”。
平復內心的悸動。挑了挑眉,對自己說。就當是場豔遇吧。躺到床上時已經是淩晨時分,很疲倦。但那雙眼睛一直在眼前,揮之不去。我有絲驚異,那不過是個陌生人。
突然後知後覺地想起,他說的是韓語。天殺的!那個讓人心動的男人居然是我最最討厭的男人品種!要命,我要速速忘記他。
海老大大發慈悲,要請大家吃東西。有人提議去千鶴。我第一個舉手:“饒了我吧,我現在看見那個招牌就想吐。”這樣說好象蠻對不起那壽司師傅,但我不想再回到事發現場。過分神經質??小心駛得萬年船。結果我們去了另一家日本料理店。我原本不討厭吃日本菜,再無異議。跟在一群男生後頭走進店裡,不過停下來問了和服小姐幾句話。海老大在叫了。“阿白你還在磨蹭什麼?什麼不好學,學別人向美女搭訕。”

咖啡店裡飄蕩著柔和的音樂,我們兩個坐在靠窗的軟沙發裡。
“阿白,我那結婚禮物已經快發黴。”她開始老生長談。
我埋頭吃霜淇淋。“張老大怎麼忍受得了你?你一次比一次囉嗦。”
她瞪我。“你少來這一套。成天混在男人堆裡,也不知道順手抓一個。你以為你還經得起拖?”
“喂喂喂,別這樣說話。”我抗議。“人家會以為我做特種行業的。”
旁邊有人用餐巾掩著嘴咳嗽。我自眼角掃過去,是一名黑衣男子。echo大眼瞪著我,終於忍不住笑出來。echo是熱情如火的女子,愛恨分明。這些年來,她一直是我的陽光。我們準備走的時候,小姐微笑地說。“那位先生已經替二位買單了。”

我與echo大眼瞪小眼。呵,我們一起混這麼久,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事。難得我們一個男人婆,一個黃臉婦,居然還有這等榮幸。那黑衣男子似乎正與人談話。他朝我點頭示意,漂亮的臉上露出一個微笑。居然是他!那個“豔遇”。
害我一路上受echo嚴刑拷問。末了,她說,“我看這傢伙心懷不軌。你自己要當心。”
我鬼祟地笑。“幾分鐘前還有人叫我抓緊身邊的男人。你不是在嫉妒我吧?”
她橫我一眼。懶得理你!我送她到家。她拎著大包小包下車。走了兩步又回頭來,臉上是難得地認真。“阿白,答應我。小心那個洋鬼子。”

我不由自主點點頭。她滿意了。擺擺手讓我走。
慢,我有說過他是韓國人嗎?
若我問echo,她會說。“哼,還用得著說麼?看那一副低級的樣子就知道!”echo一向眼光獨到。說真的,我自己對這個人也有點不安。以一個陌生人而言,他實實在在帶給我意外的情感困擾。好在我不知道他是誰,而我也不認為我們還會有第三次的“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