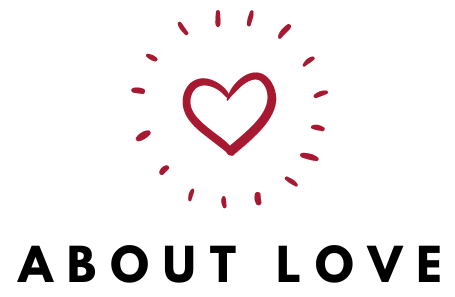撇開無知的孩童時代,我的第一段友誼開始於初中。它極其正規,對方是班裡的學霸,才貌雙全,人見人愛。長得花容月貌也就算了, 還七竅玲瓏,七竅玲瓏也就算了,還勤奮刻苦,每學期的年級第一都是她。
以至於全校的男生都組成英雄聯盟,抱著團的想超過她。我當時無知者無畏,身為她的同桌,近水樓臺先得月,和她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職責大致分為以下幾類:陪她上廁所,幫她發作業,替她擋情書。那時的我沒什麼等級意識,也還沒太弄明白“自卑”的滋味,就這樣豪情萬丈的跟在她身後,她指東,我美顛顛的跑到東,她指西,我就立馬掉頭奔向西。
直到有一天下晚自習,她的車鏈子掉了,眼看暮色低垂,她家又遠,我急的氣喘吁吁的去求助,早就餓的饑腸轆轆的男生們以為是我的車,毫不在意,直到聽見胡同深處她的化骨綿聲, 才爭先恐後的扔下車奔著她的黑影跑去。
昏黃的路燈下,我第一次感覺到我們倆是那麼的不一樣。多年後看到《甄嬛傳》裡的安陵容,雖陰險冷酷,但那句“姐姐你什麼都有”,到底辛酸。
就這樣,我開始重新審視我們的友誼,,開始發奮努力。
但是生活不是連續劇,醜小鴨最後能變成白天鵝,不是因為它有多勤奮,而是因為它是一枚天鵝蛋。
我努力了兩年半,最好成績是全班第9,物理還會偶爾掛科,身高至今也沒超過158,所以到了初中畢業,還是沒有人願意為我修車。
但她已經早早的被內定保送本校高中精英班,家裡掛著爺爺和國家領導人的握手照,假期還會和父母漂洋過海走親訪友,我們註定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老子說“企者不立, 跨者不行”,絕對是真理,上趕著不是買賣,這句話不單單適用於愛情。
就這樣,我目送她漸行漸遠,親手埋葬了我在友誼道路上的初戀。
很多年後,她驚鴻一瞥的出現在某本雜誌裡,我才知道她大學讀的是外交學院,一年後就被保送到美國深造,連年的全額獎學金,某薩俱樂部會員,現在任聯合國某公益機構秘書長。
這樣的成就我一點都不吃驚,在她的人生軌跡中不可能有半點我的位置,或者說我沒有能力與她同行太遠。
在我思量報一本還是二本的時候,她在世界各地遊歷參觀、留學講演。在我計算工資漲了三百還是五百的時候,她裝修著倫敦近郊的別墅,喝著西班牙的lamancha,在我左手鏟子,右手鍵盤的時候,她考下了飛行員和深潛證。
這樣的友誼即使當時沒有懸崖勒馬,大抵也逃不過無疾而終。我只是憑藉一己之力大大縮短了中間的過程。
工作後我一直小心謹慎,君子群而不党,在女人多的地方最好就是無幫無派,孑然一身。
我獨行了很久,竟然在一個豔陽高照的下午淪陷了。新來的同事是一個辣妹,有著凹凸的身材和火辣的颱風,和我的小格子一步之遙。

於是她迅速劃定了自己的勢力範圍,像紫霞仙子一樣隨手一個圈,把我也圈了進去。此後吃飯下班必須報備,男的不管,只要和女性同事單獨出去,都要帶上她,以示我倆對友誼的忠貞。
她對我極好,記得我生日,我媽生日,我姥姥生日,我兒子生日,統統精心DIY親手製作小禮物,搞得三姑六婆都知道我有一位驚天地泣鬼神的資深閨蜜,我倆情比金堅,海枯石爛。
我從沒被人如此重視過,記憶裡第一段友誼帶來的精神創傷瞬間被治癒,我成了那個發號施令的主導者。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非常享受這種感覺,我覺得我太幸運了, 而立之年不僅有體貼的老公,懂事的兒子,還有如此珍貴的友情。
慢慢的我發現,其實我更喜歡和冷靜平和的人待在一起,熱情讓我害怕,因為我付不出同等的熱情。
這位辣妹太年輕,她當時選中我是因為我們辦公室座位鄰近,這種不負責的“閃婚”後患無窮,隨著認識的不斷加深,我們的興趣愛好相去甚遠。
我是宅到家,她是走天涯,我是泡灶台,她是混吧台,在如今兩年一代溝的嚴峻形勢下我們的共同語言越來越少,相見不如懷念,沒話找話的尷尬實在難堪,以前強制性的每週一聚慢慢拖到一個月,半年。
再後來她有了新的圈定物件,再後來我倆見面只剩寒暄,再後來偶爾聯繫只剩點贊。
我開始意識到在愛情不易的今天,友情也難一帆風順。兩個人要想成為莫逆之交必須要門當戶對,這不單單指家世身份,年齡血型,還有價值觀、人生觀、星座觀都得匹配,否則就會一同出發,兩頭到岸。
第三段友誼發生在三年前,我因為兒子上學搬到了母親家,碰巧和一位其他部門的同事做了鄰居,我倆窗戶對窗戶,樓門挨著樓門。有時她媽包餃子,一抬腳的工夫就送到了我的餐桌上,別人送了好酒好煙,我也惦記著給她家一份。
慢慢的,我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上班一道下班,一輛26女車載著我不太肥碩的身軀風裡來雨裡去。有一天下大暴雨,我打不著車,她非要騎車帶我回家,狂風肆虐,吹得我倆東倒西歪,她還回身幫我壓著我的簡易雨衣,怕我著涼。
看著她淩亂的背影,濕漉的頭髮,被我禁錮在內心深處的友情又蠢蠢欲動死灰復燃,我以32歲的高齡開啟了一段認真的友情,這一次,我覺得又可以相信友情了。
她是個很實在的姑娘,交給她辦的事情你可以放一百個心。可惜有些矮胖,容貌不算上乘,以至蹉跎到現在。她媽媽明裡暗裡托了我愛人好幾次,要他在單位給物色個合適的對象。
我家那位屬於靦腆型,自己的事情都不好意思打聽,更不要說是敏感話題了。慢慢的,阿姨心裡起了嫌隙,覺得我們不賣力氣。

之後我在單位越幹越順,職務越升越高,年底被派到美國分公司培訓。她本也是競爭對手之一,後來因為還處在未婚,發展方向不明確在最後一刻被刷了下來。
此後她成了負能量離子團,在單位就像怨婦一樣的細數周圍人的種種不堪,稍微增加一點工作量就上綱上線推三阻四,回到家就馬不停蹄的四處相親,遍地撒網,可惜年齡太大屢戰屢敗。
我看她這樣心裡很不舒服,好容易找到了個年齡合適的小夥子介紹給她,又因為她發現男方只是個大專生而怒髮衝冠,找我理論了半天。
她冰冷的看著我,說我總是高高在上,說我一直瞧不起她,說我故意找了個大專生來羞辱她。
她一件事一件事的和我對質,自顧自的分析我每一句話背後的深深惡意,推測我尚未說出口的無禮和輕視,我聽著這些話,腦海裡浮現出了那個大雨裡無比堅強的背影,那些熱氣騰騰的餃子,還有友情被喚醒時的那種溫暖與踏實。
毫無懸念,我又重回孤獨,在與孤獨糾纏惡鬥的三十年裡,我卻發現此刻沒那麼害怕孤獨了。
我們恐懼孤獨也許只因我們對生活對自我的失控。
我的每一段無疾或有疾的友情都死於我心中的迷惘和彷徨,我們不敢單打獨鬥,可是結伴而行又太多牽絆約束,稍不同步就會前功盡棄兩敗俱傷。
經歷了這三段無疾而終的友情,我才明白,以“友誼”為名的交情大多刻意負累。
歲月沉澱,不持執念缺留在身邊的才是知我懂我的人,我們在似水流年中偶有交集,淡淡的靜靜的彼此關懷,各自修行。遼闊必然疏遠,這是我們友情的墓誌銘。
友情也難一帆風順。兩個人要想成為莫逆之交必須要門當戶對,這不單單指家世身份,年齡血型,還有價值觀、人生觀、星座觀都得匹配,否則就會一同出發,兩頭到岸。
第三段友誼發生在三年前,我因為兒子上學搬到了母親家,碰巧和一位其他部門的同事做了鄰居,我倆窗戶對窗戶,樓門挨著樓門。有時她媽包餃子,一抬腳的工夫就送到了我的餐桌上,別人送了好酒好煙,我也惦記著給她家一份。
慢慢的,我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同上班一道下班,一輛26女車載著我不太肥碩的身軀風裡來雨裡去。有一天下大暴雨,我打不著車,她非要騎車帶我回家,狂風肆虐,吹得我倆東倒西歪,她還回身幫我壓著我的簡易雨衣,怕我著涼。
看著她淩亂的背影,濕漉的頭髮,被我禁錮在內心深處的友情又蠢蠢欲動死灰復燃,我以32歲的高齡開啟了一段認真的友情,這一次,我覺得又可以相信友情了。
她是個很實在的姑娘,交給她辦的事情你可以放一百個心。可惜有些矮胖,容貌不算上乘,以至蹉跎到現在。她媽媽明裡暗裡托了我愛人好幾次,要他在單位給物色個合適的對象。
我家那位屬於靦腆型,自己的事情都不好意思打聽,更不要說是敏感話題了。慢慢的,阿姨心裡起了嫌隙,覺得我們不賣力氣。

之後我在單位越幹越順,職務越升越高,年底被派到美國分公司培訓。她本也是競爭對手之一,後來因為還處在未婚,發展方向不明確在最後一刻被刷了下來。
此後她成了負能量離子團,在單位就像怨婦一樣的細數周圍人的種種不堪,稍微增加一點工作量就上綱上線推三阻四,回到家就馬不停蹄的四處相親,遍地撒網,可惜年齡太大屢戰屢敗。
我看她這樣心裡很不舒服,好容易找到了個年齡合適的小夥子介紹給她,又因為她發現男方只是個大專生而怒髮衝冠,找我理論了半天。
她冰冷的看著我,說我總是高高在上,說我一直瞧不起她,說我故意找了個大專生來羞辱她。
她一件事一件事的和我對質,自顧自的分析我每一句話背後的深深惡意,推測我尚未說出口的無禮和輕視,我聽著這些話,腦海裡浮現出了那個大雨裡無比堅強的背影,那些熱氣騰騰的餃子,還有友情被喚醒時的那種溫暖與踏實。
毫無懸念,我又重回孤獨,在與孤獨糾纏惡鬥的三十年裡,我卻發現此刻沒那麼害怕孤獨了。
我們恐懼孤獨也許只因我們對生活對自我的失控。
我的每一段無疾或有疾的友情都死於我心中的迷惘和彷徨,我們不敢單打獨鬥,可是結伴而行又太多牽絆約束,稍不同步就會前功盡棄兩敗俱傷。
經歷了這三段無疾而終的友情,我才明白,以“友誼”為名的交情大多刻意負累。
歲月沉澱,不持執念缺留在身邊的才是知我懂我的人,我們在似水流年中偶有交集,淡淡的靜靜的彼此關懷,各自修行。遼闊必然疏遠,這是我們友情的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