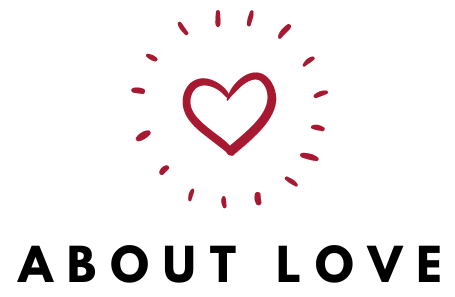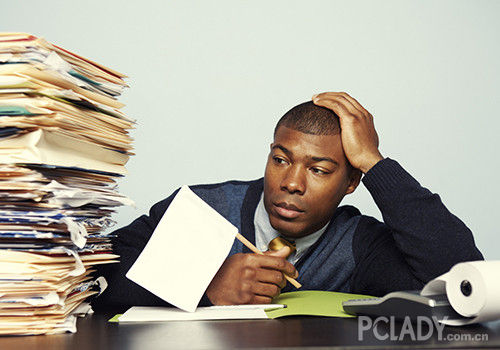晝信基督夜信佛
作者:史鐵生(著名作家、散文家)
大概是我以往文章中流露的混亂,使得常有人問我:你到底是信基督呢,還是信佛法?我說我白天信基督, 夜晚信佛法。
這回答的首先一個好處是誰也不得罪。怕得罪人是我的痼疾,另方面,信徒們多也容易被得罪。當著佛門弟子讚美基督,或當著基督徒頌揚佛法,你會在雙方臉上看到同樣的表情:努力容忍著的不以為然。
這表情應屬明顯的進步,若在幾十年前,信念的不同是要引發武鬥與迫害的。但我不免還是小心翼翼,只怕那不以為然終於會積累到不可容忍。
怕得罪人的另一個好處,是有機會兼聽博采,算得上是因禍得福。麻煩的是,人們終會看出,你哪方面的立場都不堅定。
可信仰的立場是什麼呢?信仰的邊界,是國族的不同?是教派的各異?還是全人類共通的理性局限,以及由之而來的終極性迷茫?
人的迷茫,根本在兩件事上:一曰生,或生的意義;二曰死,或死的後果。倘其不錯,那麼依我看,基督教誨的初衷是如何面對生,而佛家智慧的側重是怎樣看待死。
這樣說可有什麼證據嗎?為什麼不是相反——佛法更重生前,基督才是寄望於死後?證據是;大凡向生的信念,絕不會告訴你苦難是可以滅盡的。為什麼?很簡單,現實生活的真面目誰都看得清楚。清楚什麼?比如說:樂觀若是一種鼓勵,困苦必屬常態;堅強若是一種讚譽,好運必定稀缺;如果清官總是被表彰呢,則貪腐勢力必一向強大。
在我看,基督與佛法的根本不同,集中在一個“苦”字上,即對於苦難所持態度的大相徑庭。前者相信苦難是生命的永恆處境,其應對所以是“救世”與“愛願”;後者則千方百計要遠離它, 故而祈求著“往生”或“脫離六道輪回”。而這恰恰對應了白天與黑夜所向人們要求的不同心情。
外面的世界之可怕,連小孩子都知道。見過早晨幼稚園門前的情景嗎?孩子們望園怯步,繼而大放悲聲;父母們則是軟硬兼施,在笑容裡為之哭泣。聰明些的孩子頭天晚上就提前哀求了:媽媽,明天我不去幼稚園!
成年人呢,早晨一睜跟,看著那必將升起的太陽發一會兒愣,而後深明大義:如果必須加入到外面的世界中去,你就得對生命的苦難本質說是。否則呢?否則世上就有了“抑鬱症”。
待到夕陽西下,幼稚園門前又是怎樣的情景呢?親人團聚,其樂陶陶,完全是一幅共用天倫的動人圖畫!及至黑夜降臨, 孩子在父母含糊其詞的許諾中睡熟;父母們呢,則是在心裡一遍遍祈禱,一遍遍驅散著白天的煩惱,但求快快進入夢的黑甜之鄉。倘若白天揮之不去,《格爾尼卡》式的怪獸便要來禍害你一夜的和平。
所以,基督信仰更適合於苦難充斥的白天。他從不作無苦無憂的許諾,而是要人們攜手抵抗苦難,以建立起愛的天國。
譬如耶穌的上十字架,一種說法是上帝舍了親子,替人贖罪,從而彰顯了他無比的愛願。但另一種解釋更具深意:創世主的意志是誰也更改不了的,便連神子也休想走走他的後門以求取命運的優惠,於是便逼迫著我們去想,生的救路是什麼和只能是什麼。

愛,必是要及他的,獨自不能施行。
白天的事,也都是要及他的,獨自不能施行。
而一切及他之事,根本上有兩種態度可供選擇:愛與恨。
恨,必致人與人的相互疏遠,相互隔離,白天的事還是難於施行。
惟有愛是相互的期盼,相互的尋找與溝通,白天的事不僅施行,你還會發現,那才是白天裡最值得施行的事。
白天的信仰,意在積極應對這世上的苦難。
佛門弟子必已是忍無可忍了:聽你的意思,我們都是消極的嘍?
非也,非也!倘其如此,又何必去苦苦修行?
夜晚,是獨自理傷的時候,正如歌中所唱:“這故鄉的風,這故鄉的雲,幫我撫平傷痕。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
你曾經到哪兒去了?傷在何處?
我曾赴白天,傷在集市。在那兒,價值埋沒于價格,連人也是一樣。
所以就,“歸來吧!歸來喲!別再四處漂泊……”
夜晚是心的故鄉,存放著童年的夢。夜晚是人獨對蒼天的時候:我為什麼要來?我能不能不來,以及能不能再來?“死去原知萬事空”,莫非人們累死累活就是為了最終的一場空?空為何物?死是怎麼回事?死後我們會到哪兒去?“我”是什麼?靈魂到底有沒有?……黑夜無邊無際,處處玄機,要你去聽、去想,但沒人替你證明。
白天(以及生)充滿了及他之事,故而強調愛。黑夜(以及死)則完全屬於個人,所以更要強調智慧。白天把萬事萬物區分得清晰,黑夜卻使一顆孤弱的心連接起浩瀚的寂靜與神秘,連接起存在的無限與永恆。所謂“得大自在”,總不會是說得一份大號的利己之樂吧?而是說要在一個大於白天、乃無窮大的背景下,來評價自我,於是也便有了一份更為大氣的自知與自信。
“自在”一詞尤其值得回味。那分明是說:只有你——這趨於無限小的“自”,與那無邊無際趨於無限大的“在”,相互面對、相互呼告與詢問之時,你才能確切地知道你是誰。而大凡這樣的時刻,很少會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更多地發生於隻身獨處的黑夜。
倘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拘泥於這一個趨於無限小的“我”,煩惱就來了。所謂“驅散白天的煩惱”,正是要驅散這種對自我的執著吧。
執著,實在是一種美德,人間的哪一項豐功偉績不是因為有人執著於斯?惟執迷才是錯誤。但如何區分“執著”與“執迷”呢?常言道“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執於前者即是美德,執於後者便生煩惱。所以,其實,一切“迷執”皆屬“我執”!用一位偉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話說,就是“我的重要性”——一切“迷執”都是由於把自我看得太過重要。那巫士認為,只因在“我的重要性”上耗費能量太多,以致人類蠅營狗苟、演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動物。所以狹隘,更在於這動物還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來標定世界的真相。
那巫士最可稱道的品質是:他雖具備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功能,但並不以此去沽名釣譽;他雖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另類存在,但並不以此自封神明,只信那是獲取自由的一種方式;他雖批評理性主義的狹隘,卻並不否定理性,他認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動、追求那無邊的寂靜中所蘊含的完美知識,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這世界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無論局限於哪一種都會損害生命的自由。這樣,他就同時回答了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無論生死,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
是嘛,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但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進步、繁榮、公正?那只能是階段性的安慰,其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說,一條無始無終的路,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才不至陷於荒誕。
基督信仰的弱項,在於黑夜的匱乏。愛,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但是死呢?虛無的威脅呢?無論多麼成功的生,最終都要撞見死,何以應對呢?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偉大創造、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這是最大的、也是最終的問題。
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萬事空”,憑什麼認為“及時行樂”不是最聰明的舉措?既是最聰明的舉措,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可那樣的話,誰還會顧及什麼“可持續性發展”?進而,為了“及時行樂”而巧取豪奪他人——乃至他族與他國——之美,豈不也是順理成章?
“但悲不見九州同”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家祭無忘告乃翁”,就連“王師北定中原日”也難彌補“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悲涼與荒誕。所以我還是相信,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

當然,哲學難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協。那是因為,次一等的政制也比無政府要好些,但絕不等於說哲學本身也要退讓。倘若哲學也要隨之退一等,便連城邦的好壞也沒了標準,還談的什麼妥協!妥協與同流合污畢竟兩碼事。
佛法虛無嗎?恰恰相反,他把“真”與“有”推向了無始無終。而死,絕不等於消極,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全面地看看生前與死後都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換一個白天所不及的角度,看看我們曾經信以為真和誤以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麼一回事……
故而,佛法跟科學有緣。說信仰不事思辨顯然是誤解,只能說信仰不同於思辨,不止於思辨。佛門智慧,單憑沉思默想,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學幾千年後才弄懂的事;比如“惟識”一派,早已道出了“量子”的關鍵。還有“薛定鍔的貓”——那只可憐的貓呵!
便又想到醫學。我曾相信中醫重實踐、輕理論的說法,但那不過是因為中醫理論過於艱深,不如西醫的解剖學來得具體和簡明。中醫理論與佛家信念一脈相承,也是連接起天深地遠,連接起萬事萬物,把人——而非僅僅人體——看作自然整體之局部與全息。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縛(比如禮儀習俗),使之在人體解剖方面有失仔細。而西醫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招招落在實處,對於人體的機械屬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徹,手段高超。比如器官移植,比如史鐵生正在享用著的“血液透析”。
要我說,所謂“中西醫結合”,萬不可弄成相互的頂替與消耗,而當各司其職,各顯其能;正如晝夜交替,陰陽互補,熱情與清靜的美妙結合。
不過,說老實話,隨著科學逐步深入到納米與基因層面,西醫正在彌補起自身的不足,或使中醫理念漸漸得其證實也說不定。不過,這一定是福音嗎?據說納米塵埃一旦隨風飛揚,還不知人體會演出怎樣的“魔術”;而基因改造一經氾濫,人人都是明星,太陽可咋辦!中醫就不會有類似風險——清心寡欲為醫,五穀百草為藥,人倫不改,生死隨緣,早就符合了“低碳”要求。不過這就好了嗎?至少我就擔心,設若時至1998年春“透析”技術仍未發明,史鐵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歲了,哪還容得我六十歲上晝信基督夜信佛!
處處玄機,要你去聽、去想,但沒人替你證明。
白天(以及生)充滿了及他之事,故而強調愛。黑夜(以及死)則完全屬於個人,所以更要強調智慧。白天把萬事萬物區分得清晰,黑夜卻使一顆孤弱的心連接起浩瀚的寂靜與神秘,連接起存在的無限與永恆。所謂“得大自在”,總不會是說得一份大號的利己之樂吧?而是說要在一個大於白天、乃無窮大的背景下,來評價自我,於是也便有了一份更為大氣的自知與自信。
“自在”一詞尤其值得回味。那分明是說:只有你——這趨於無限小的“自”,與那無邊無際趨於無限大的“在”,相互面對、相互呼告與詢問之時,你才能確切地知道你是誰。而大凡這樣的時刻,很少會是在人山人海的白天,更多地發生於隻身獨處的黑夜。
倘若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拘泥於這一個趨於無限小的“我”,煩惱就來了。所謂“驅散白天的煩惱”,正是要驅散這種對自我的執著吧。
執著,實在是一種美德,人間的哪一項豐功偉績不是因為有人執著於斯?惟執迷才是錯誤。但如何區分“執著”與“執迷”呢?常言道“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執於前者即是美德,執於後者便生煩惱。所以,其實,一切“迷執”皆屬“我執”!用一位偉大的印第安巫士的話說,就是“我的重要性”——一切“迷執”都是由於把自我看得太過重要。那巫士認為,只因在“我的重要性”上耗費能量太多,以致人類蠅營狗苟、演變成了一種狹隘的動物。所以狹隘,更在於這動物還要以其鼠目寸光之所及,來標定世界的真相。
那巫士最可稱道的品質是:他雖具備很多在我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神奇功能,但並不以此去沽名釣譽;他雖能夠看到我們所看不到的另類存在,但並不以此自封神明,只信那是獲取自由的一種方式;他雖批評理性主義的狹隘,卻並不否定理性,他認為真正的巫士意在追求完美的行動、追求那無邊的寂靜中所蘊含的完美知識,而理性恰也是其中之一。我理解他的意思是:這世界有著無限的可能性,無論局限於哪一種都會損害生命的自由。這樣,他就同時回答了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無論生死,都是一條無始無終地追求完美的路。
是嘛,歷史並不隨某一肉身之死而結束。但歷史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進步、繁榮、公正?那只能是階段性的安慰,其後,同樣的問題並不稍有減輕。只有追求完美,才可能有一條永無止境又永富激情的路。或者說,一條無始無終的路,惟以審美標準來評價,才不至陷於荒誕。
基督信仰的弱項,在於黑夜的匱乏。愛,成功應對了生之苦難。但是死呢?虛無的威脅呢?無論多麼成功的生,最終都要撞見死,何以應對呢?莫非人類一切美好情懷、偉大創造、和諧社會以及一切輝煌的文明,都要在死亡面前淪為一場荒誕不成?這是最大的、也是最終的問題。
據說政治哲學是第一哲學,城邦利益是根本利益,而分清敵我又是政治的首要。但令我迷惑的仍然是:如果“死去原知萬事空”,憑什麼認為“及時行樂”不是最聰明的舉措?既是最聰明的舉措,難道不應該個個爭先?可那樣的話,誰還會顧及什麼“可持續性發展”?進而,為了“及時行樂”而巧取豪奪他人——乃至他族與他國——之美,豈不也是順理成章?
“但悲不見九州同”確是一種政治的高尚,但信心分明還是靠著“家祭無忘告乃翁”,就連“王師北定中原日”也難彌補“死去原知萬事空”的悲涼與荒誕。所以我還是相信,生的意義和死的後果,才是哲學的根本性關注。

當然,哲學難免要向政治做出妥協。那是因為,次一等的政制也比無政府要好些,但絕不等於說哲學本身也要退讓。倘若哲學也要隨之退一等,便連城邦的好壞也沒了標準,還談的什麼妥協!妥協與同流合污畢竟兩碼事。
佛法虛無嗎?恰恰相反,他把“真”與“有”推向了無始無終。而死,絕不等於消極,而是要根本地看看生命是怎麼一回事,全面地看看生前與死後都是怎麼一回事,以及換一個白天所不及的角度,看看我們曾經信以為真和誤以為假的很多事都是怎麼一回事……
故而,佛法跟科學有緣。說信仰不事思辨顯然是誤解,只能說信仰不同於思辨,不止於思辨。佛門智慧,單憑沉思默想,便猜透了很多物理學幾千年後才弄懂的事;比如“惟識”一派,早已道出了“量子”的關鍵。還有“薛定鍔的貓”——那只可憐的貓呵!
便又想到醫學。我曾相信中醫重實踐、輕理論的說法,但那不過是因為中醫理論過於艱深,不如西醫的解剖學來得具體和簡明。中醫理論與佛家信念一脈相承,也是連接起天深地遠,連接起萬事萬物,把人——而非僅僅人體——看作自然整體之局部與全息。倒是白天的某些束縛(比如禮儀習俗),使之在人體解剖方面有失仔細。而西醫一直都在白天的清晰中,招招落在實處,對於人體的機械屬性方面尤其理解得透徹,手段高超。比如器官移植,比如史鐵生正在享用著的“血液透析”。
要我說,所謂“中西醫結合”,萬不可弄成相互的頂替與消耗,而當各司其職,各顯其能;正如晝夜交替,陰陽互補,熱情與清靜的美妙結合。
不過,說老實話,隨著科學逐步深入到納米與基因層面,西醫正在彌補起自身的不足,或使中醫理念漸漸得其證實也說不定。不過,這一定是福音嗎?據說納米塵埃一旦隨風飛揚,還不知人體會演出怎樣的“魔術”;而基因改造一經氾濫,人人都是明星,太陽可咋辦!中醫就不會有類似風險——清心寡欲為醫,五穀百草為藥,人倫不改,生死隨緣,早就符合了“低碳”要求。不過這就好了嗎?至少我就擔心,設若時至1998年春“透析”技術仍未發明,史鐵生便只好享年四十七歲了,哪還容得我六十歲上晝信基督夜信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