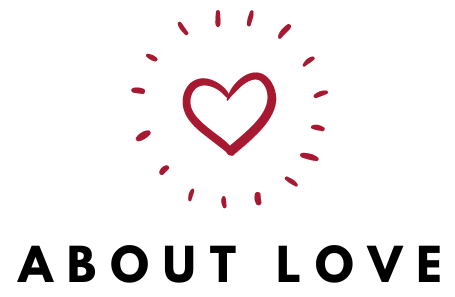本文是美國作家大衛.歐文回憶自己少年時代學習生活時寫的一篇文章。它塑造了一個對學生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又獨具一格的老師。 他告訴了我們,每個人講的話都不一定是正確的,要有敢於懷疑的精神。
原文欣賞編輯
懷特森先生教我們六年級的科學課。第一節課上,他問我們:“誰知道一種叫做凱蒂旺普斯的動物?”同學們面面相覷(qù),就連生物比賽得過獎的比利也都驚奇地瞪大了眼睛。
“噢,沒有人知道。”懷特森老師笑了笑,“那是一種夜行獸,在冰川期無法適應環境的變化而絕跡了。”說著,他從講桌裡拿出一件動物頭骨,向我們解釋起這種動物的特徵來。講完,他把頭骨交給前排的同學,讓大家輪流觀察一下。我們饒有興趣地傳看,記筆記,有的同學還畫了圖。我心中暗想,這回我遇到一位博學的老師了。
第二天,懷特森老師對上次講的內容進行了測驗, 我胸有成竹地答好了卷子,交給老師。
可是,當試卷發下來的時候,我卻驚呆了:我答的每道題旁邊都打著大大的紅叉!怎麼同事?我完完全全是按照老師講的寫的呀!一定有什麼地方弄錯了。我瞧瞧周圍的同學,似乎每一個同學都不及格,比利正氣惱地捶桌子呢。這是怎麼回事呢?

“很簡單,”懷特森老師眼裡閃過狡黠(jiǎoxiá)的光芒,解釋道,“有關凱蒂旺普斯的一切都是我編造的,這種動物從來就沒有過。你們筆記裡記的都是錯的,錯的當然就不能得分了。”
“從來沒有過?那你那天拿的頭骨是怎麼回事?”比利問。
“那件頭骨嘛,”懷特森老師笑了,“不過是馬的頭骨罷了。”
那你為什麼要在課堂上鄭重其事地講?為什麼還要考試,這種老師算什麼老師?一股怒火升上了我的心頭,我緊緊抿(mǐn)住嘴唇,控制著自己不嚷出來。教室裡響起了不滿的議論聲。
懷特森老師擺擺手,讓大家平靜下來:“難道你們沒有想過嗎?既然已經‘絕跡’了,我怎麼可能那麼詳盡地描述它的夜間視力、皮毛的顏色, 以及許多根本不存在的現象,還給它起了個可笑的名字,你們竟一點兒也沒有起疑心,這就是你們不及格的原因。”

懷特森老師說試卷上的分數是要登記在成績冊上的,他也真這麼做了。他希望我們從這件事上學到點兒什麼。
上懷特森老師的課, 每一節都是不尋常的探索。比如,有一次他說小轎車是活的生物,讓我們反駁。我花了整整兩天時間寫小論文,說明小轎車和生物不一樣。他看了後說:“勉強及格,你總算知道了什麼是生物,什麼不是。”
漸漸地,我們懂得了,書本上寫的,老師說的,並不是一貫正確的,事實上沒有誰是一貫正確的。我們應該時刻保持警惕,用事實,用科學的方法,糾正錯誤,而且應當有堅持真理的毅力。同學們把這種學習方法稱為“新懷疑主義”。
我們把“新懷疑主義”帶進了所有的課堂。每堂課我們都十分注意聽講。有時老師講著講著,下面就會有同學清清嗓子,說:“凱蒂旺普斯。”接著他站起來,正視著老師的眼睛,說出懷疑的理由。這樣做是很有趣的。 當然,多數的時候,我們懷疑錯了,但老師在糾正我們的錯誤時,就加深了我們對事物的理解;有時我們的懷疑是正確的,它又促使老師去糾正錯誤。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識到這裡面的價值。有一次,我把懷特森老師的事講給一位鄰居,他驚訝極了:“那位老師不該這樣捉弄你們。”我正視著他的眼睛,告訴他:“不,你錯了。”
主要內容編輯
本文寫了懷特森先生教“我們”六年級的科學課時,他運用“故弄玄虛策略“使”我們”認識到傳統的一套是有問題的,培養了“我們”以“新懷疑主義”態度對待事物的習慣,也讓“我們”產生了探索科學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