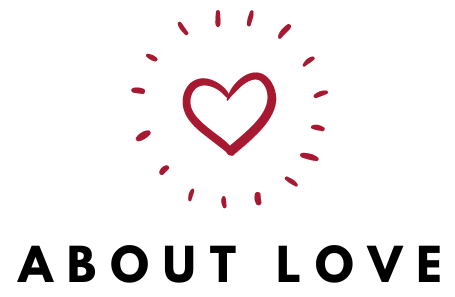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減輕情傷帶來的痛苦?也許做夢可以幫助到你哦。因為做夢有宣洩和調節情緒的作用, 可以幫忙減輕痛苦、度過艱難的失戀期。
從周公到佛洛德,對夢都沒能給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但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從未停止探索夢的腳步,提出了五花八門的學說。在解釋了我們為什麼做夢?,之後,他們又要講一講夢在現實生活的奇妙益處,例如,睡著覺做著夢就把學過的東西複習了,夢境幫助我們調節負面情緒,以及教我們如何把噩夢變成刺激的享受。

夢境的奧妙
睡著覺做著夢也能學習,這不是做夢。先從睡眠階段講起。睡眠的一個週期有兩個時相:非快速眼動睡眠期(NREM)和快速眼動睡眠期(REM)。REM期眼球快速運動,做夢正酣;不過夢並非REM期特有,NREM期也有零星的夢境,只是沒有前者的鮮活生動。

夢境有重播功能,如果你剛玩過滑雪遊戲,在隨後的NREM期可能會夢見滑雪。大腦掃描研究也顯示,清醒時大腦神經元的活動模式在隨後的NREM期會重現。REM期夢境也會反映先前所學,只是表現得有點變形–滑過雪後可能不會夢見雪,而只是從山上沖下來。

除了重播,更重要的是夢對記憶的鞏固、整合和分類。重播當天的5-7天后,相關夢境可能又會出現。人們猜測這是由於海馬區整合短期記憶以將之變為長期記憶在大腦皮層儲存下來的過程中,整理時的記憶碎片會在夢裡呈現,織出一個個荒誕離奇的故事。碎片出現的順序或許反映了大腦如何將記憶分解成片段再整合存儲的。大腦在加工資訊的過程中甚至會翻舊賬,找出新的經歷與故人故事的關聯。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會夢見多年不見的朋友或地方。

目前尚不清楚哪一時相的夢執行了什麼樣的功能。有人認為NREM期的夢主要是鞏固記憶,而REM期夢境則能整合記憶,將新經歷融入我們的記憶庫裡。可是也有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假說。不管真相如何,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兩種夢對學習記憶都頗有裨益,夢見先前學習內容的人們,之後會有更好的表現。

做夢可以調節情緒
人們清醒的時間越長,越容易被生氣或憂慮等負面情緒影響。此時如果來個小憩,做做夢,會使人們對負面情緒沒那麼敏感,情緒也更加積極,但只有REM期的夢才有效。不過在記憶鞏固時,REM期的夢似乎格外偏愛帶有負面情緒的那些。聽起來不妙,卻不一定是壞事。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如果記不住,何以長智?此外,研究者們也認為,做夢時重播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同時免于親身經歷時的生理和情緒變化,可以使得我們接受那些經歷,最終放下。經歷過痛苦的人們,所做的夢也格外生動,畫面感強,夢中記憶也更清晰,這或許也反映了大腦是在如何艱難地接納和整合這些資訊。

拉什大學的羅莎琳·卡萊特(Rosalind Cartwright)在1960年開始跟蹤研究那些經歷了離婚、分離或喪親之痛的人們,發現經常夢見痛苦經歷的人能更好地應對以後的生活。因此,失戀後一時難以接受怎麼辦?多做幾個夢吧。高度情緒化的夢,最終會撫平我們情緒上的傷痕。可惜的是在創傷後應激障礙者身上這一過程會失效,他們做夢時也會伴隨強烈的情緒反應。

如同記憶處理一樣,REM和NREM期的夢在調節情緒方面也可能角色不同。從不同的時相醒來的人們敘說的夢,其性質大有不同。NREM期的夢帶有更多友好元素,而REM期裡人們夢見的未知和威脅因素更多,負面情緒更強。這裡引出了噩夢的進化學解釋。

噩夢也有積極作用
並非人人都討厭噩夢,芬蘭的心理學家安蒂·瑞文蘇(Antti Revonsuo)就挺享受噩夢,至少在事後是如此。他覺得,噩夢像一場事先不知道只是電影的絕佳恐怖片,還不會被劇透(除了反復做同樣噩夢的情況)。他認為夢的精髓在於噩夢,因為噩夢能讓我們為應對來自真實世界的危險提前進行演練。健康成年人2/3的夢裡都有某種威脅,例如被人追殺、陷入爭鬥等。瑞文蘇認為,由於兒童尚未充分接觸現代社會,他們的夢更能反映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所遭遇的危機。比起成年人,兒童的噩夢更多,芬蘭兒童超過一半的夢裡都有威脅元素,在飽經憂患的巴勒斯坦兒童身上,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3/4。另一證據是兒童所做的夢裡,40%-50%會出現不友善的動物,似乎是我們祖先野外生活的寫照,而西方成年人的夢只有5%會有可怕動物。

在夢裡我們常常會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後面有追擊者,怎麼老是邁不開腿呢!如果能主動出擊控制夢的情節走向該有多好。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加拿大麥科文大學的簡妮·加肯巴赫(Jayne Gackenbach)關於遊戲與夢境的研究,她發現遊戲玩家對夢有更強的控制感,不是坐以待斃,而會主動出擊,將可怕的噩夢變成打怪一般的刺激享受。這或許可以用來幫助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們。所以,噩夢實際上也有一種調節的作用。

沉溺遊戲並不是個好主意,我們也可以試試十九世紀的夢學研究專家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的氣味法。當時他為了避免自己的主觀期待影響結果而採用了單盲法:吩咐他的僕人隨機擇日在他的枕邊灑香水,結果發現會夢見與相關氣味關聯的場景。或許我們也可以使用中意的氣味來引導產生愉悅的夢境。

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失戀也是如此,失戀之後難免會沉浸在消逝的感情中不可自拔,夢境會讓你看清自己的內心所想,從而有了向前走的勇氣。
聽起來不妙,卻不一定是壞事。所謂吃一塹長一智,如果記不住,何以長智?此外,研究者們也認為,做夢時重播那些不愉快的經歷,同時免于親身經歷時的生理和情緒變化,可以使得我們接受那些經歷,最終放下。經歷過痛苦的人們,所做的夢也格外生動,畫面感強,夢中記憶也更清晰,這或許也反映了大腦是在如何艱難地接納和整合這些資訊。

拉什大學的羅莎琳·卡萊特(Rosalind Cartwright)在1960年開始跟蹤研究那些經歷了離婚、分離或喪親之痛的人們,發現經常夢見痛苦經歷的人能更好地應對以後的生活。因此,失戀後一時難以接受怎麼辦?多做幾個夢吧。高度情緒化的夢,最終會撫平我們情緒上的傷痕。可惜的是在創傷後應激障礙者身上這一過程會失效,他們做夢時也會伴隨強烈的情緒反應。

如同記憶處理一樣,REM和NREM期的夢在調節情緒方面也可能角色不同。從不同的時相醒來的人們敘說的夢,其性質大有不同。NREM期的夢帶有更多友好元素,而REM期裡人們夢見的未知和威脅因素更多,負面情緒更強。這裡引出了噩夢的進化學解釋。

噩夢也有積極作用
並非人人都討厭噩夢,芬蘭的心理學家安蒂·瑞文蘇(Antti Revonsuo)就挺享受噩夢,至少在事後是如此。他覺得,噩夢像一場事先不知道只是電影的絕佳恐怖片,還不會被劇透(除了反復做同樣噩夢的情況)。他認為夢的精髓在於噩夢,因為噩夢能讓我們為應對來自真實世界的危險提前進行演練。健康成年人2/3的夢裡都有某種威脅,例如被人追殺、陷入爭鬥等。瑞文蘇認為,由於兒童尚未充分接觸現代社會,他們的夢更能反映我們的祖先在遠古時代所遭遇的危機。比起成年人,兒童的噩夢更多,芬蘭兒童超過一半的夢裡都有威脅元素,在飽經憂患的巴勒斯坦兒童身上,這一比例甚至達到了3/4。另一證據是兒童所做的夢裡,40%-50%會出現不友善的動物,似乎是我們祖先野外生活的寫照,而西方成年人的夢只有5%會有可怕動物。

在夢裡我們常常會覺得心有餘而力不足–後面有追擊者,怎麼老是邁不開腿呢!如果能主動出擊控制夢的情節走向該有多好。常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是加拿大麥科文大學的簡妮·加肯巴赫(Jayne Gackenbach)關於遊戲與夢境的研究,她發現遊戲玩家對夢有更強的控制感,不是坐以待斃,而會主動出擊,將可怕的噩夢變成打怪一般的刺激享受。這或許可以用來幫助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的人們。所以,噩夢實際上也有一種調節的作用。

沉溺遊戲並不是個好主意,我們也可以試試十九世紀的夢學研究專家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的氣味法。當時他為了避免自己的主觀期待影響結果而採用了單盲法:吩咐他的僕人隨機擇日在他的枕邊灑香水,結果發現會夢見與相關氣味關聯的場景。或許我們也可以使用中意的氣味來引導產生愉悅的夢境。

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失戀也是如此,失戀之後難免會沉浸在消逝的感情中不可自拔,夢境會讓你看清自己的內心所想,從而有了向前走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