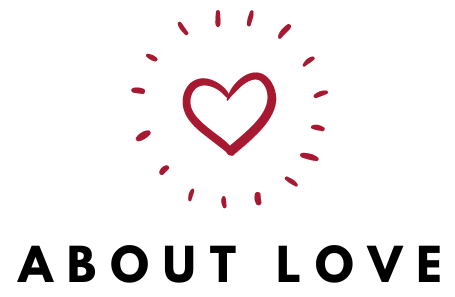美國作家,哲學家亨利·大衛·梭羅關於孤獨的一篇唯美散文:孤獨是一個人的狂歡
在這美妙的黃昏,我的身心融為一體,大自然的一切尤顯得與我相宜。
夜幕降臨了,風兒依然在林中呼嘯,水仍在拍打著堤岸,一些生靈唱起了動聽的催眠曲。伴隨黑夜而來的並非寂靜,猛獸在追尋獵物。這些大自然的更夫使得生機勃勃的白晝不曾間斷。
我的近鄰遠在一英里開外,舉目四望,不見一片房舍,只有距我半英里地的黑黢黢的山峰。四周的叢林圍起一塊屬於我的天地。遠方鄰近水塘的一條鐵路線依稀可辨,只是絕大部分時間,這條鐵路像是建在莽原之上,少有車過。這兒更像是在亞洲或非洲,而不是在新英格蘭,我獨享太陽、月亮和星星,還有我那小小的天地。
然而,我常常發現,在任何自然之物中,我們都可以找到天真無邪,令人鼓舞的夥伴。對於生活在大自然之中的人來說, 永遠沒有絕望的時候。我生活中的一些最愉快的時光,莫過於春秋時日陰雨連綿獨守空房的時刻。
人們常常問我:“你一個人住在那兒一定很孤獨,很想見見人吧,特別是在雨雪天裡。”
我真想這樣回答他們:“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不也只是宇宙中的一葉小舟嗎?我為什麼會感到孤獨呢?我們的地球不是在銀河系之中嗎?”將人與人分開並使其孤獨的空間是什麼?我覺得使兩顆心更加親近的不是雙腿。
試問,我們最喜歡逗留何處?當然不是郵局,不是酒吧,不是學校,更非副食商店;縱使這些場所使人摩肩接踵。我們不願住在人多之處,而喜歡與自然為伍,與我們生命的不竭源泉接近。
我覺得經常獨處使人身心健康。 與人為伴,即便是與最優秀的人相處也會很快使人厭倦。我好獨處,迄今我尚未找到一個夥伴能有獨處那樣令我感到親切。當我們來到異國他鄉,雖置身於滾滾人流之中,卻常常比獨處家中更覺孤獨。孤獨不能以人與人的空間距離來度量。一個真正勤勉的學生,雖置身於擁擠不堪的教室之中,也能像沙漠中的隱士一樣對周圍一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整天在地裡除草或在林中伐木的農夫雖只孤身一人卻並不感到孤獨,這是因為他的身心均有所屬。但一旦回到家裡,他不會繼續獨處一方,而必定與家人鄰居聚在一起,以補償所謂一天的“寂寞”。於是,他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學生怎麼能整夜整天地單獨坐在房子裡而不感到厭倦與沮喪。 他沒能意識到,學生儘管坐在屋裡卻正像他在田野中除草,在森林中伐木一樣。
社會已遠遠背離“社會”一詞的基本意義。儘管我們接觸頻繁,但卻沒有時間從對方身上發現新的價值。我們不得不格守一套條條框框,即所謂“禮節”與“禮貌”,才能使這頻繁的接觸不至於變得不能容忍而訴諸武力。在郵局中,在客棧裡,在黑夜的篝火旁,我們到處相逢。我們擠在一起,互相妨礙,彼此設障,長此以往,怎能做到相敬如賓?毫無疑問,相互接觸的適當減少決不會影響我們之間的重要交流。假如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住一個人——就像我現在這樣,那將更好。人的價值不在其表面,我們需要的是深刻的瞭解, 而非頻繁卻淺薄的接觸。
身居陋室,以物為伴,獨享閒情,尤當清晨無人來訪之時。我想這樣來比喻,也許能使人對我的生活略知一斑:我不比那嬉水湖中的鴨子或沃爾登湖本身更孤獨,而那湖水又何以為伴呢?我好比茫茫草原上的一株蒲公英,好比一片豆葉,一隻蒼蠅,一隻大黃蜂,我們都不感到孤獨。我好比一條小溪,或那一顆北極星;好比那南來的風,四月的雨,一月的霜,或那新居裡的第一隻蜘蛛,我們都不知道孤獨。